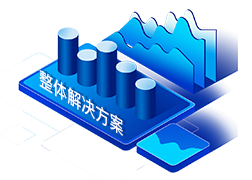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要推動技術改造升級,促進制造業數智化轉型,發展智能制造、綠色制造、服務型制造,加快產業模式和企業組織形態變革。傳統制造業的高端化是通過數字化、綠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方式,從低端產業升級為高端產業,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躍升。其中智能化是技術上的“硬骨頭”,也是全球未能攻克的難關。實現傳統制造業的智能化升級,是“中國智造”的關鍵支撐,也是“人工智能+”行動的重要任務,必須高度重視、系統謀劃,探索務實舉措加快推進。
制造業創新的底層邏輯
傳統制造業智能化的本質,是通過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賦能機器高效柔性完成復雜生產,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性能,構建柔性制造體系以響應市場需求。當前,剛性操作已基本實現自動化或初步智能化,但依賴人工的柔性操作仍是制約制造系統效能提升、阻礙產業高端化的核心瓶頸。需明確的是,柔性操作的智能化并非孤立的技術突破,而是嵌入產業場景的系統性創新。正因如此,制造業的智能化升級離不開一個由技術、裝備、產品、市場、生態五大要素構成的閉環創新系統。其中,市場需求首先傳導至產品部門,催生新產品需求;產品需求進一步驅動裝備部門開發新型制造裝備;而裝備升級又倒逼技術部門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只有當這五個環節緊密銜接、高效協同,重大創新才具備落地生根的土壤。一旦閉環斷裂,創新便如無本之木,難以形成可持續的產業升級動能。
美國曾憑借這一創新閉環長期引領全球制造業的創新發展,但隨著產業空心化、產品部門外移,裝備部門繼而塌縮,生態也滑入脫實向虛的軌道,創新閉環斷裂,其主導的技術創新被迫轉向脫離制造業場景的通用技術研究,其特點是聚焦“起點評估”(從起點前進了多遠),逃避“終點評估”(距離終點還有多遠),因為脫離了應用場景就不存在可觀察、可考核的創新終點。由此造成制造業“從0到1”創新成果不足以支撐后續“從1到N”創新的連帶效應。一個顯著表現是,1988年美國學者提出的智能制造至今未能落地。這一教訓表明,創新閉環斷裂必然阻斷從制造到智造的升級之路,還會引發經濟全球化失衡、社會撕裂與創新體系失效等連鎖反應。
我國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5年居全球首位,其中80%為傳統制造業,向“智造”轉型既是必由之路,更是當務之急。從全球格局看,我國具備成為全球智造引領者的獨特條件,但制造業仍面臨技術與裝備、產品、市場銜接不暢、創新生態不完善、知識產權保護亟待強化等問題。在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新興技術領域,最新成果與我國制造業升級的實際需求相對脫節,這更凸顯了加快構建制造業技術、裝備、產品、市場、生態協同創新閉環的緊迫性。
以新型創新實體激活制造業內生動力
在以往的產學研合作模式中,企業往往難以獲得產業創新的主導地位,來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發團隊也難以擺脫所在單位的管理機制及評價體系的制約,難以扭轉脫離應用場景的思維習慣。這種情況下,技術、裝備、產品、市場、生態五大部門之間并沒有真正打通,致使產學研合作的實際效果不理想。
為此,需結合傳統制造業不同細分行業的技術特性、產業鏈布局,以及不同地區的產業基礎差異,在政府政策引導與資源支持下,由具備技術引領能力的龍頭企業、擁有科研實力的研發機構牽頭,聯合本細分行業及上下游的其他企業、研發機構和社會組織,共同組建新型創新實體。這類實體不僅能從組織架構上串聯起技術、裝備、產品、市場、生態五大核心部門,根除傳統體制下的協同壁壘,更能通過“研發協同、中試銜接、生產革新、人才集聚、市場賦能”的五維協同模式,精準解決產業創新脫節、成果轉化不暢、生產模式滯后等內循環痛點,系統性推動傳統制造業向智能化、融合化升級,真正實現制造業內生發展閉環的破局提質,解決內循環的問題。
一是研發協同,錨定需求,打通產學研鏈路。新型創新實體需明確研發機構的核心職責,聚焦本創新實體發展中的共性技術需求開展關鍵技術突破、核心裝備研發、先進工藝優化等攻關任務,同時與外部高校、科研院所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機制以推動產學研深度協同。通過這一模式,可實現產業創新方向與產業升級實際需求的無縫對接,有效破解高校及科研院所與產業需求脫節、龍頭企業持續創新動力不足、大批中小企業創新能力薄弱等行業痛點。
二是中試銜接,貫通創新全鏈條。由龍頭企業和研發機構共建中試平臺,支撐技術、工藝、裝備等創新研發成果的測試、驗證和優化,將“從0到1”創新與“從1到N”創新的一體化落到實處,打通創新鏈條中的關鍵堵點,加速創新成果向實際生產力轉化。
三是生產革新,重構生產組織模式。在新型創新實體中共享創新成果,逐步實現智能化柔性制造及相應的新型生產組織,實行柔性生產、集約化生產、產線租賃、委托生產等多種靈活的生產組織形式,不再局限于以量取勝的傳統生產模式和最大化行業集中度的發展路徑,糾正將產業升級等同于減人增效的方向誤判。
四是人才集聚,構建新型人才生態。由新型創新實體統一招聘、培養和使用研發人才、現代化管理人才和高技術員工,解決傳統制造業企業對各類人才吸引力不強的問題,探索實施適應“中國智造”人才需求的新型人才戰略。
五是市場賦能,破除發展體制障礙。面向從制造到智造升級產生的大量新現象、新經驗和新問題,探索符合“中國智造”客觀規律的市場理論、發展理念和經濟體制,破除傳統理論、理念和體制對“中國智造”、智能社會的阻礙。
主動融入全球產業協作
在完成內循環體系搭建、夯實“中國智造”產業根基后,要實現全球競爭力的突破,還需以更主動的姿態參與全球產業協作,構建適配“中國智造”的外循環體系,其中實現“中國智造”與全球高增量發展區域協同發展正是這一格局的核心載體。
從全球產業版圖演變來看,未來30年世界將逐步形成“高質量發展區域、高消費區域、高增量發展區域”三大核心板塊,而我國憑借制造業規模優勢與智能化升級潛力,正成為推動全球產業變革的關鍵動力。其中,以東南亞、拉丁美洲、南亞、非洲、中東及中亞為代表的高增量發展區域,近年來已快速成長為傳統制造業的重要增長極。它們既向歐美高消費區域輸出物美價廉的消費品,自身也面臨迫切的產業升級需求,對技術、裝備、生態的依賴正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智造”。
與這類高增量發展區域不同,我國正逐步進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階段——當務之急是加快建成技術、裝備、產品、市場、生態的創新閉環,率先實現傳統制造業智能化升級,成為全球高質量發展核心區域。這一轉型將推動我國從以往主要向高消費區域輸出物美價廉的產品,逐步轉變為向高增量發展區域(和其他區域)有序輸出先進的、高質量的技術、裝備、產品、市場和生態資源,形成“中國智造”外循環與全球高增量發展區域協同發展的格局,并與“中國智造”的內循環一體化運行,塑造與創新全球化相融合的新型經濟全球化。
在這一協同發展格局下,我國作為未來全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區域,與高增量發展區域將基于各自比較優勢實現深度協作:我國有序輸出先進的智造資源,助力高增量發展區域突破產業升級瓶頸;高增量發展區域則提供廣闊市場空間與產業配套需求,反哺“中國智造”技術迭代與生態完善,最終實現經濟成長的互惠共贏與推動文明交流互鑒。
構建多維度協同保障體系
“中國智造”的推進需依托系統性、協同性的新型舉國體制,通過整合多方資源、優化制度設計,在創新實體、服務支撐、國際協同等維度形成合力,為產業升級提供堅實保障。
一是打造新型創新實體。在政府引導與支持下,探索以多元社會力量新型組合形態構建“中國智造”的創新實體,推動創新要素高效聚合、形成合力。同時保持機制與運作層面的充足靈活性,動態適配產業創新的現實需求,確保創新活力持續釋放。
二是完善行業服務體系。依托政府的統籌協調與支持保障,優化制造業各細分行業協會的職能定位,既要做好國內行業發展的統籌協調,也要為各類創新主體提供精準適配的行業服務,為產業創新筑牢服務支撐。
三是構建國際協調體系。在政府的統籌推動與支持賦能下,以創新主體為核心、行業協會為紐帶,構建“中國智造”與全球高增量發展區域協同發展格局,推動國內外對口行業的對接合作與戰略溝通,落實知識產權、行業標準、倫理規范的區域化、國際化協調發展。
四是優化成果評價體系。消除論文等級、數量等不利于智造創新的考核指標干擾,對產業創新的實際貢獻進行分類梳理,涵蓋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工程創新等關鍵維度,并針對不同類型貢獻制定科學、精準的評價指標。
五是創新知識產權保護模式。深化和拓展“開源”思想,探索構建適合“中國智造”和高質量發展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共享體系。
六是健全人才培養體系。加快建設智造創新的人才培養體系。將相關學科的工科教育融入創新閉環,使人文社科教育與“中國智造”和全球高增量發展區域協同發展格局相關聯;提高職業化教育的水平;擴大“卓越工程師”計劃的培養范圍并推動培養模式的社會化,從以高校為主轉變為以創新主體為主;淡化對高學歷的過度重視,以實際能力和具體成效作為人才培養目標和評價標準。
七是培育新型創新文化。實現從制造到智造的產業升級,需要從業人員與社會各界推動思維方式從產品生產導向轉為價值創造導向。為此,需突破傳統創新理念的束縛,加快發展適配智造需求的創新理論,構筑支撐產業轉型的新型創新文化,為“中國智造”發展提供思想動力與文化保障。
(作者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機器人實驗室主任、廣東省科學院人工智能首席科學家)
來源:學習時報
免責聲明:本網站部分文章、圖片等信息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平臺所有,僅用于學術分享,如不慎侵犯了你的權益,請聯系我們,我們將做刪除處理!